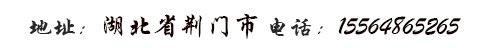作文大赛二等奖作品柳木尺
|
柳木尺 广西师范大学莫倩莹 01 宋宇恨了后院里的那棵柳树十一年。他盯着柳树下嬉戏上的小孩,人脚下的影子又深又扁,这种影子让人想到湖,又或者养热带鱼的鱼缸。鱼缸被放入五彩斑斓的热带鱼,人落入自己的影子。“哥哥,哥哥!”一个小孩跑过来扯了扯他衣服下摆,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,嘴角还沾着刚吃完的糖渣,一张口就漏风,本该长着两颗门牙的位置空荡荡的,说话都口齿不清,“哥哥,宋叔叔过年的时候会回来吗?”一提到那个男人,宋宇就感觉内心的烦躁就像掉落的碳酸汽水一样,碎成一串串泡沫从胸腔涌上来,他抹掉小孩嘴边的糖渣,“他不会回来的。”他三岁的时候男人便去参加了国际维和,从此以后,“父亲”这个陌生的名词就像断了线的风筝,有时候是一年,有时候是三年,男人只会停留一两天,然后又像蒲公英一样飘向远方。后来,母亲也离开了家。小的时候,宋宇站在院子里,看着老太太对着那棵挺拔的柳树咒骂,说都怪这棵柳树招邪,害得他们家四离五散。男人回来的时候,老太太说要砍了这柳树,男人不让,老太太红着眼睛大骂,“册那,脑子缺盖啊!”而回应她的只有男人抿着的沉默的唇线。那天晚上,老太太便不愿意和男人一起吃饭了,自己摊了个小木桌支棱着。小木桌和饭桌的距离,后来竟成了母子之间数十年的隔阂。当时七岁的宋宇目睹着一切,恨意好像在心中透明的陷阱里浮沉,变成虚无的鱼往玻璃缸边缘游弋,柔软的身体穿过玻璃缸游走在小木桌和饭桌的距离之间,游到后院的那棵柳树上。他盯着院子里的柳树恨恨地想,是不是因为词语里国总是在家的前面,所以才让他的童年既没有爸爸,也没有妈妈。02. 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冷。宋宇下了课走在街上,看着路灯盏盏亮起,灯下的雪花温柔地落在地上,临近过年,街上比平时冷清了许多。桥头边卖小馄饨的铺子也准备收摊了。雪越下越大,在他眼睫上积了薄薄的一层白霜。小桥流水与人家,船舶靠在青石板的岸边,沿河的店铺已经挂上了灯笼,漫天飘雪间,两岸灯火明晃晃地倒映在水里。老太太撑着伞,仿佛只是等了他一会,伞上的积雪却出卖了她。“好婆。”宋宇接过她手里的伞柄,“等很久了吧。”老太太拍干净他身上的雪渣子,“你要是真心疼我,就多收着心放在读书上,别成天拎勿清,课本东西不识一点,没记性,青肚皮猢狲!”宋宇没说话,他的脸颊贴着老太太的白发轻轻蹭了蹭。男人也拍过他的肩膀和他说到了高中就要好好读书。当时他只是狠狠地甩开了搭在他肩上的手臂,理智犹如点燃的蜡烛,能够存在的形状渐渐化为无踪。男人管过他吗?他有为自己操心过一次吗?他有把自己当成过亲生儿子爱过吗?他现在怎么好意思堂而皇之地教育他?他好像是不怀好意地开口,“那是因为别人有爸妈教,我没有。”在看到男人黯淡的神情后他仿佛获得了一种胜利性的报复般的快意。所有美好都在这一瞬间枯萎凋零,沙沙沙,心里那条鱼从鱼缸里一路下坠,最终碎成了泡沫。只剩带着委屈的黄昏,受伤的脸庞。那天男人从柳树上折了一枝树枝,好像要做什么。临走的时候,男人在他书桌上放了一把尺子,柳木做的,纹路清晰,一看就是被人细细打磨过的。“下次爸爸和你去逛轧神仙好不好?”一直到男人离开,宋宇都没说过一句话。心中仿佛撕开了一个口,把恨意步步为营的城池突然一口吞并成一片眩晕的白光,又幻灭散落成无数颗粒,变成了浮游的弧光。那些光点慢慢聚落在一起。是那条游弋的鱼。它游在那把尺子上。宋宇看也没看便把那把尺子扔进了第二个抽屉里。“他今年还是不回来。”老太太低落的话语把他从回忆里拽了出来。“嗯。”他站在桥上,一低头就能看见夜游的乌篷船,摇橹的人唱着歌,一竿子划碎了两岸灯笼的照影,长龙蜿蜒过桥头岸边,点燃了粉墙黛瓦与飞檐翘角。03. 男人回来的时候是在春末。宋宇正一个人坐在桥墩上,脚下是清波绿,远处的乌篷船的船尾停了一只鸬鹚,在夕阳下眯着眼扇了扇翅膀,摇橹的人扔了条鱼,又长又重的木浆轻轻地磕了磕船舷,鸬鹚伸直了细长的脖颈,一个猛子扎进水里。来告诉他的是隔壁的陈叔,急匆匆地跑来,大声道,“宋宇你爸回来了,但是……但是……”那人神色间都是惊慌,话都不会说了。他心一沉,推开那人大步跑回家里。老式的洋房外头半边墙上爬满了爬山虎,客厅很暗,穿堂风带着院子里泥土的湿气。宋宇刚刚进去,远远看到客厅里站着几个穿着维和制服的人,其中一个捧着一个大大的黑白相框,脚一软差点跪了下去,还是旁边的陈叔及时扶住了他。宋宇闭了闭眼睛,强稳住心神走过去,看清相框里的人后,心脏都快撕裂了。相片上的男人他很熟悉,可覆在上面的黑白色却让他觉得陌生。宋宇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,脑子里一片空白,他下意识想要去找好婆。阳光洒满了院子里的围墙,风吹起地上的叶子沙沙作响,好婆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。宋宇走进院子,“好婆?”她枯坐在那,双眼空洞地盯着眼前的柳树,没有理会任何人。柳树结了许许多多的柳絮,风一吹,白绒绒得像雪一样落了好婆满肩头。那天的柳絮落得格外地大。李远鹏看着眼前脸色苍白的少年回头问他,“是骗人的对不对?”少年像一株白杨,安静地站在那里,春色露出温柔的眉目,自他肩颈罅隙间穿透而来的几缕春光却阴冷得有些刺眼,像是要把所有的谎言戳破。李远鹏握紧了相框,声音喑哑,“宋国锋同志,我们带你回家了。”眼前的少年表情狰狞,他讽刺地一笑,眼眶却更红了,“家?这里不是他的家!他把这里当过家吗?他有一天想过我们吗?他哪有什么家可回!”说完,便丢下所有人跑走了。04. 宋宇冲进房间里打开书桌第二个抽屉从里面扯出那把柳木尺,一头往家门外跑。今天正是轧神仙,商铺琳琅满目,夹道吆喝,不少小孩都骑在大人肩上,看底下全是一片人头攒动。街两边挂上了灯笼,广场上立着八仙铜像,有姑娘扮成何仙姑,挎着竹篮卖荷花和莲蓬,舞台上开始演八仙过海。锣鼓声喧天,舞龙舞狮的队伍也加入了进来,何仙姑抛起一只荷花样子的绣球,长龙在河边蜿蜒游走。宋宇抓着那把柳木尺,一头扎进人群,拨开两侧的人往前跑。在夜色里,灯火通明的建筑物变成了无数巨兽的齿牙,吞吃着每一个人的痛苦和懦弱,无数恨意的波涛在他心里翻滚挣扎,同时保持静默。周围人来人往,他却浑身冰凉,孑然一身。他好像在人群里看到一群面目模糊的人,影影绰绰,夹杂着像雾看不清的脸,慢慢聚拢合成一个人影,是那个男人。他不顾一切地往男人在的方向冲,有关于男人的黑的白的回忆融化解封,冰冷的月光刺骨地穿透膝盖骨,那样撕心裂肺的痛苦只经历一次都铭刻一生,像是无处躲藏的悲伤如影随形,它们变成了在身后出现的可怕魔鬼,伸出锋利的手爪,只要宋宇一跌倒,它们就能把他整得面目全非。他最终还是承受不住悲伤的重量,失魂落魄地蹲在路边,发出长长的一声哭嚎,哽在胸腔和喉头之间,周围的人不明所以地诧异地看着他,宋宇用力地折断了那把柳木尺。断成两半的柳木尺就像宋宇和男人之间轰塌的桥梁。生与死的距离,宋宇永远无法跨越。05. “好婆,我是医生,现在需要我们,我们是必须要去支援的。”宋宇耐着性子和眼前已经耆耆老矣的好婆解释。老太太却红肿着眼睛一个字也听不进去,颤颤巍巍地走进院子里拿起拐杖吃力地砸向那棵柳树,歇斯底里地哭骂,“都是这棵柳树!都是这棵柳树!你还想怎么样?夺走了我的儿子还想抢走我的孙子吗?我要把你砍了!我要把你……砍了!”宋宇把挣扎的老婆按进怀里,“好婆,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的。”方才还哭闹的老太太顿时静了下来,拐杖从她手里滑落。那天晚上,好婆走进他的房间,什么也没说,只是在他桌子上留下了一张光盘和断成两半的柳木尺。宋宇播放了光盘里的视频,摇摇晃晃的镜头里粗糙的画面,南苏丹风景很美,连绵的白色难民帐篷之上是日出和落霞烧红半边天,泥泞的黄土路在大片大片的丛林中延伸到天边。这样美的国家,却天天响起枪声。随处可见城市的废墟,汽车炸弹袭击后只随便铺了白布就摆在道路两旁的尸体,炮火停息后的南苏丹,祷告的教堂安静而神圣。镜头里的男人用着蹩脚的英语教当地的小孩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China,“拆那。”一旁的李远鹏止不住笑,“宋国锋你英语不行啊!是China。”小孩愣愣地抬起头问,“China是什么意思?”“China是叔叔的祖国。”“祖国是什么?”“从心脏处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土地的距离。”男人冲着镜头,对牢了他的眼睛,“就是祖国。”那个断成两半的柳木尺,宋宇从来没有仔细看过,打磨得光滑的平面上,一笔一画刻着,“宋宇,成人。”他捧着断成两半的柳木尺跪在院子里,皮肤底下那些奔腾叫嚣的红色河流承载着他最隐秘的痛往返于周身,一次又一次围绕内脏和骨髓将他拽入悔意的复杂循环里。宋宇曾经在男人离开的第五年去了瑞士的马特洪峰。在登到峰顶的那一刻,他看着匍匐在地平线上的高大雪山,它们仿佛是这个世界尽头被人遗忘的物种,孤独而寂寞地簇拥在这里,彼此安慰,等待着有人的来临。那里的冰雕师说,想念一个人,就像冰灯里装着火焰,很快就会融化了。曾经他以为男人就像马特洪峰,那里该是一片天寒地冻的无情,所以自己永远不会在梦里和男人相见。但是现在,他终于学会了想念。“宋国锋。”他抓着那把柳木尺放到心脏处,“爸爸,我来带你回家了。”06. 出发去支援的那天动员大会上,有眼尖的护士发现宋宇脖子上戴着一个从未见过的小木片,便打趣道,“宋医生,你脖子上挂着的是什么啊?”宋宇低头抚摸那小木片,“是片柳木。”“柳木?”护士被挑起了好奇心。“嗯,是从很重要的东西上截下来的一片。”“那上面应该会刻什么吧?是健康还是平安啊?”宋宇抬头笑了一下,就像男人在他九岁时教他说China,就像男人在南苏丹教当地的小孩拼China一样,露出一个充满希望的笑来。“是China。”往期精彩回顾▼动物饲养员和马戏团的大象徒名之樱70年,公里更多精彩推荐,请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pugongyinga.com/pgyxy/802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乙肝患者能喝蒲公英茶吗
- 下一篇文章: 人到中年后,每天来一坏蒲公英茶,这3个好